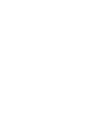32.我来送你
这一日之后,他们正式分手,手机偶尔联系,可他发送的频率断崖式减少,他放下自尊,热脸贴冷屁股,换不来她的心软。
她发来很长一段文字,全是绝情的话,让他不要再烦扰,放过她,甚至将他拉入黑名单。他笑了,怀疑自己被她耍,可他亦发现她一旦下决心就不受动摇,态度十分决绝。
有一天,他们拿到考试成绩开毕业典礼,结束之后是庆功会,姚伶到场,他们时隔两个月相见。大家都知道两人关系出问题,然而他们的社交账号还没删除照片。
坦白说,他们被父母送到这个老牌又有点国际化的高中读了叁年,眼界和觉悟都摆在那里,自然祝福姚伶的选择,却为他们闹僵感到可惜。
这种奇怪的关系持续到姚伶的手续办下来,他们一家把房子卖掉,收拾好行李,买了凌晨叁点从香港机场出发的国际航班。
啤梨和林哲与姚伶疏远起来,因为他们看到邓仕朗被伤得很重,两个月内喝过不少酒,甚至跟父母吵架,夜不归宿。
他们没有去送行,只有小郁在晚上七点来到姚伶家楼下,抱着一个公仔,给她送别。
姚伶下来,把一本手工做好的相册送给小郁,里面都是他们的照片,有她和邓仕朗的,也有啤梨和林哲的。两人在路灯下抱着,小郁哭得很伤心,她理解邓仕朗的心情,但这是她最好的朋友,她希望好朋友能过得更好。
“别哭了。”姚伶说完,抹眼,“你再哭,我会忍不住的。”
“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在那边怎么样。”小郁哭到拿袖子擦脸。
姚伶点头,眼泪掉下来,“我知道,你也是。”
分开之后,小郁目送她上车,一直挥手,等她走了,小郁的眼泪都滴到手机,给邓仕朗发消息,告诉他快去香港机场送姚伶。
凌晨十二点,他们一家已经到香港机场值机。姚伶抱着小郁的公仔,在安检门口看到一个人在打电话。她的手机响了,心一痛,转过头,不想再看。
邓仕朗握着手机寻找她,见到她之后,走到她面前,依然没有挂断。她的铃声响好久,是《Loving You》。
“我来送你。”他放下手机,站在他面前。
姚伶抓着公仔的绒毛,看到他虽然有些疲倦,但还是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看。她用很生疏的口吻回复:“不用那么麻烦的。”
邓仕朗说:“我还是来了。”
恰巧,沉雨跟姚申和发现他们,邓仕朗礼貌地介绍自己。姚伶忽然说:“他是邓仕朗,我之前的男朋友。”
沉雨才明白,打量他们很久,告诉他们再过半小时就要进安检,然后带丈夫进咖啡厅,留空间。
邓仕朗抬手读表,距离凌晨叁点还有两个半小时。他指一指旁边的空位,说:“坐下吧。”
姚伶跟着他,坐下来。有五分钟,他们都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坐着。机场英粤播报,乘客脚步匆匆,停在大屏前看航班信息。偶尔有几组机务人员经过,人来人往,时间慢慢流走。
邓仕朗见她抚摸公仔的绒毛,顺了又逆,逆了又顺。他打破沉默,“你不给我任何联系方式。”
姚伶定住,轻嗯一声,“你已经伤得很厉害,再这样下去你会受不了。虽然现在很难受,但都是短暂的。”她也是这么说服自己。
邓仕朗笑了笑,“你是怎么做到现在还能这样对我。”
她低头,不自觉地捏着公仔的耳朵,“其实你早就衡量出哪个才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,只是为了你所认为的感情在犹豫。这个犹豫不会长久,再犹豫下去都是自我感动很在乎对方而已,除了精神上废弛一些,并不能获得实质结果。”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再死缠烂打下去很自私,应该尊重你的选择。”邓仕朗望着她,“你说得对,我要考虑自己,更何况我已经不是你男朋友。”
姚伶点头,尽管有些难以呼吸,她还是很高兴他们达成共识。她拿出自己的手机,手指勾着耳机,“听歌吗。”
邓仕朗没有拒绝,接过她的耳机放左耳,她则戴入右耳。耳机线连着,他们并排而坐。她播放AGA的《3AM》。
“但愿没什么拉扯与纠缠,故事维持不变……It’s 3 a.m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’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,但你应该知道我们情境多尴尬。如假开心开心开始假得很,倒不摊开这张牌……”
邓仕朗听这里再也听不下去,把耳机摘掉,还给她。
姚伶已经听过好多遍这首歌,听到麻痹不流泪,这次在他面前也可以控制得很好。她的耳边还在播放,抱好公仔,“我要进去了。”
邓仕朗站起来和她一起到安检口,目送她进去。在她越走越远时,他还是想叫住她,哪怕他知道她不会回头,也在她背后叫她名字:“伶伶。”
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,姚伶快步到他面前,放下公仔,环住他腰,不舍地说:“再见。”
“去吧。”邓仕朗知道要放手了。
姚伶松开他,一进安检见不到他,心绞痛到止不住眼泪。安检人员不知她为什么哭,拿仪器扫她的身体时,她还在抖,泪水拼命掉地上,左一滴右一滴。沉雨跟姚申和等到姚伶,发现她一直在哭,顿悟到心痛,搂着她肩膀,摸她头发。她很少这样,却在机场被他们抱着抽泣。
她发来很长一段文字,全是绝情的话,让他不要再烦扰,放过她,甚至将他拉入黑名单。他笑了,怀疑自己被她耍,可他亦发现她一旦下决心就不受动摇,态度十分决绝。
有一天,他们拿到考试成绩开毕业典礼,结束之后是庆功会,姚伶到场,他们时隔两个月相见。大家都知道两人关系出问题,然而他们的社交账号还没删除照片。
坦白说,他们被父母送到这个老牌又有点国际化的高中读了叁年,眼界和觉悟都摆在那里,自然祝福姚伶的选择,却为他们闹僵感到可惜。
这种奇怪的关系持续到姚伶的手续办下来,他们一家把房子卖掉,收拾好行李,买了凌晨叁点从香港机场出发的国际航班。
啤梨和林哲与姚伶疏远起来,因为他们看到邓仕朗被伤得很重,两个月内喝过不少酒,甚至跟父母吵架,夜不归宿。
他们没有去送行,只有小郁在晚上七点来到姚伶家楼下,抱着一个公仔,给她送别。
姚伶下来,把一本手工做好的相册送给小郁,里面都是他们的照片,有她和邓仕朗的,也有啤梨和林哲的。两人在路灯下抱着,小郁哭得很伤心,她理解邓仕朗的心情,但这是她最好的朋友,她希望好朋友能过得更好。
“别哭了。”姚伶说完,抹眼,“你再哭,我会忍不住的。”
“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在那边怎么样。”小郁哭到拿袖子擦脸。
姚伶点头,眼泪掉下来,“我知道,你也是。”
分开之后,小郁目送她上车,一直挥手,等她走了,小郁的眼泪都滴到手机,给邓仕朗发消息,告诉他快去香港机场送姚伶。
凌晨十二点,他们一家已经到香港机场值机。姚伶抱着小郁的公仔,在安检门口看到一个人在打电话。她的手机响了,心一痛,转过头,不想再看。
邓仕朗握着手机寻找她,见到她之后,走到她面前,依然没有挂断。她的铃声响好久,是《Loving You》。
“我来送你。”他放下手机,站在他面前。
姚伶抓着公仔的绒毛,看到他虽然有些疲倦,但还是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看。她用很生疏的口吻回复:“不用那么麻烦的。”
邓仕朗说:“我还是来了。”
恰巧,沉雨跟姚申和发现他们,邓仕朗礼貌地介绍自己。姚伶忽然说:“他是邓仕朗,我之前的男朋友。”
沉雨才明白,打量他们很久,告诉他们再过半小时就要进安检,然后带丈夫进咖啡厅,留空间。
邓仕朗抬手读表,距离凌晨叁点还有两个半小时。他指一指旁边的空位,说:“坐下吧。”
姚伶跟着他,坐下来。有五分钟,他们都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坐着。机场英粤播报,乘客脚步匆匆,停在大屏前看航班信息。偶尔有几组机务人员经过,人来人往,时间慢慢流走。
邓仕朗见她抚摸公仔的绒毛,顺了又逆,逆了又顺。他打破沉默,“你不给我任何联系方式。”
姚伶定住,轻嗯一声,“你已经伤得很厉害,再这样下去你会受不了。虽然现在很难受,但都是短暂的。”她也是这么说服自己。
邓仕朗笑了笑,“你是怎么做到现在还能这样对我。”
她低头,不自觉地捏着公仔的耳朵,“其实你早就衡量出哪个才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,只是为了你所认为的感情在犹豫。这个犹豫不会长久,再犹豫下去都是自我感动很在乎对方而已,除了精神上废弛一些,并不能获得实质结果。”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再死缠烂打下去很自私,应该尊重你的选择。”邓仕朗望着她,“你说得对,我要考虑自己,更何况我已经不是你男朋友。”
姚伶点头,尽管有些难以呼吸,她还是很高兴他们达成共识。她拿出自己的手机,手指勾着耳机,“听歌吗。”
邓仕朗没有拒绝,接过她的耳机放左耳,她则戴入右耳。耳机线连着,他们并排而坐。她播放AGA的《3AM》。
“但愿没什么拉扯与纠缠,故事维持不变……It’s 3 a.m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’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,但你应该知道我们情境多尴尬。如假开心开心开始假得很,倒不摊开这张牌……”
邓仕朗听这里再也听不下去,把耳机摘掉,还给她。
姚伶已经听过好多遍这首歌,听到麻痹不流泪,这次在他面前也可以控制得很好。她的耳边还在播放,抱好公仔,“我要进去了。”
邓仕朗站起来和她一起到安检口,目送她进去。在她越走越远时,他还是想叫住她,哪怕他知道她不会回头,也在她背后叫她名字:“伶伶。”
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,姚伶快步到他面前,放下公仔,环住他腰,不舍地说:“再见。”
“去吧。”邓仕朗知道要放手了。
姚伶松开他,一进安检见不到他,心绞痛到止不住眼泪。安检人员不知她为什么哭,拿仪器扫她的身体时,她还在抖,泪水拼命掉地上,左一滴右一滴。沉雨跟姚申和等到姚伶,发现她一直在哭,顿悟到心痛,搂着她肩膀,摸她头发。她很少这样,却在机场被他们抱着抽泣。